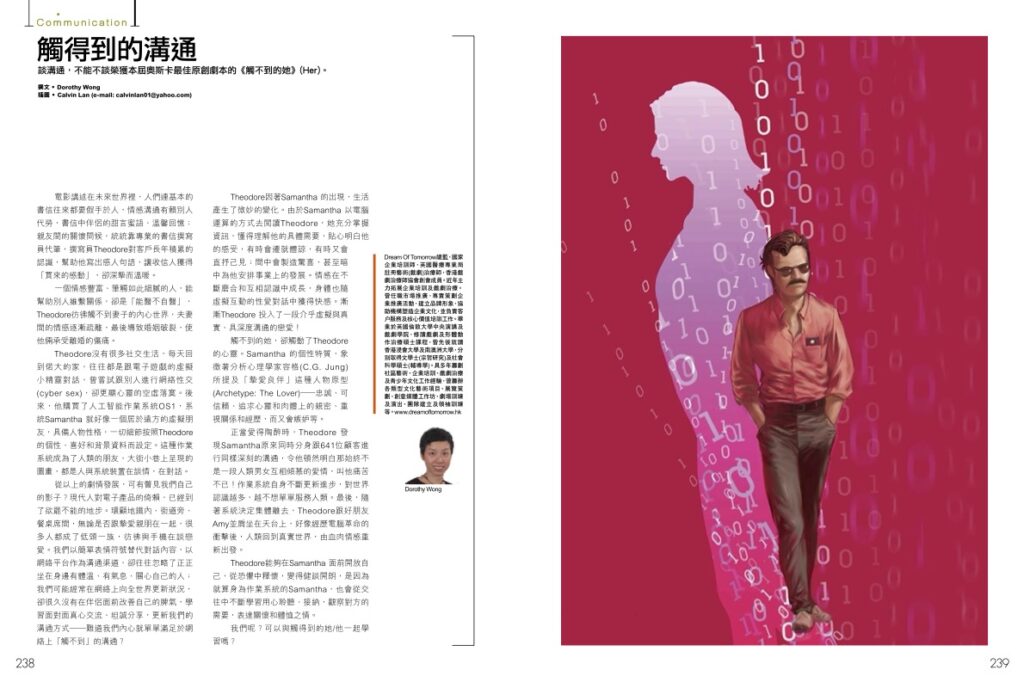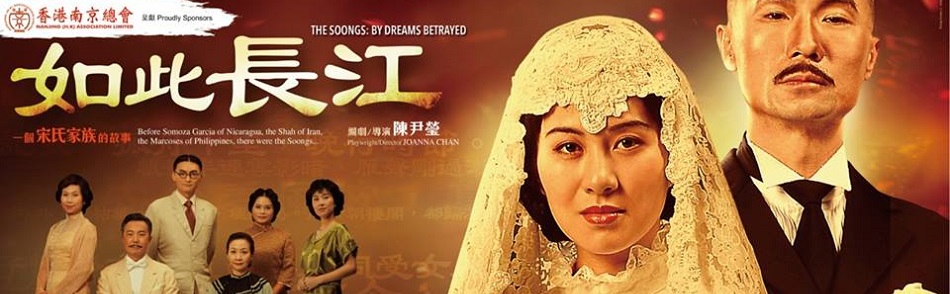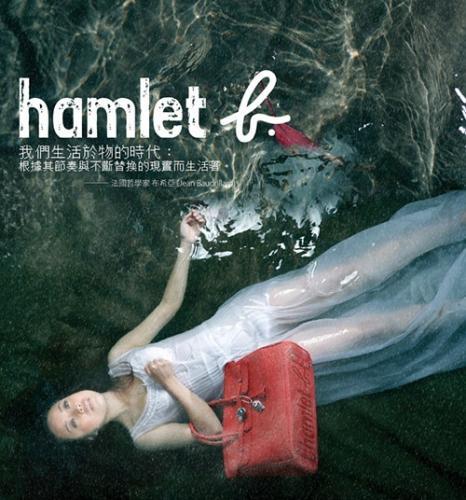講真,因為窮,說不上是劇場常客。
講真,因為懶,除非超有感,否則不常寫作。
講真,喜歡陳炳釗今次「講真」。

「只有一個入口,卻彷彿有無數個出口,它連接著香港第一個華人商區的興衰,帝國航海傳奇,填海大歷史,家族小敘事、童夢與成長。」
劇刊上這段文字總括得很好,單單數十字,巳經建構了豐富的影像。一條毫不起眼的街道,一個小小的入口,在舞台上演變出無數的可能。
這個故事是關於陳炳釗在中環鐵行里成長的故事。由陳炳釗親自敍述家中小狗的故事開始,再由演員演繹不同的「陳炳釗的故事」。以童年軼事書寫城市發展,以個人敍事(personal narrative)描繪宏觀歷史 (grand narrative),香港生活結合土耳其遊歷影象,手法是有趣的。在一個已經什麼也不能說的世代,我們除了說自己,還餘下多少可以說的呢?
今天還可以玩 Wordle說早晨,可以吃豐富早餐,可以入劇場看戲,通通都要感恩;書寫自己,也是書寫歷史洪流裏面的一滴水。這一滴水,無論有多微小,其表面張力的折射或多或少總能反映點點環境的真實,透過水流的速度和流經的地方和方向,也算是見證着歷史點滴。鐵行里在市區重建當下面臨的消失,在在提醒自己,我們又有什麼很想記下?值得記下?還是任由記憶在水流日夜沖刷下逐漸消失?

我自己比較喜歡,是當演員朱栢康與梁天尺飾演的陳炳釗出場之後的故事發展,或許,真實的故事加上戲劇的變奏再呈現,還是來得多點趣味和吸引。不是說歷史的真實、個人故事的直面演繹真實不好看,着實當中舞台的設計、燈光以及影象效果巳經把單純說故事升華了很多。然而我還是喜歡劇場空間的魔幻變奏,結合真實與虛構情節,「你以為佢講真,其實佢講假」地以假說真、以真亂假,以劇場美學重新呈現真實的文本,或許在可見的未來,是更真實地呈現真實故事更好的方法。回家後閱讀前進進劇場的「真實劇場探索計劃」小冊子,呼應着我近來在思考劇場的治癒性,可以如何回應人們真實生活裏的情感需要;怎樣的文本才具有帶治癒性的回應力?自傳式、紀錄或是記事式文本的真實,才能反映真實?赤裸裸的全然真實才是真實?怎樣的真實才是重要?
喜歡今次的舞台、燈光設計及影像製作,枱的四角設置小平台,由對稱的上落樓梯連接着,台的中央是兩段八字型台階連接三個演區,台的最前端是碼頭的繫船柱,象徵着中環臨海位置。整個設計用上大細不一的影像投射,演出全長約兩小時,一點沒有悶場,燈光和影像的變化,讓人看得很舒服,把香港一條小巷里的前世今生,在最初約半小時內就訴說了。想像自己在讀一本書,或是由一個說書人平白地讀出來,也許悶到瞓着。但一段又一段中環早期歷史,加上一幅又一幅的歷史照片,古往今來,配合台上影像的變化和演員演繹,畫面就豐富得多了。

整個故事雖然是陳炳釗導演自己真實的童年故事,其中穿插了虛構的情節,哪屬真實?哪屬虛構?對劇場觀眾而言,到底重要嗎?於我而言,重要的也許不是哪部分的內容屬於真實,重要的是參與者在當中能夠領略或體會自己真實的那部分有多少。就如哈維爾在《無權者的力量》一書中提出我們要「活在真實中」。一齣好的作品,無論文本有多少真實的成分,我看,更重要的是,讓我們能窺探和討論、甚至繼續書寫、尋索、堅持、守護屬於我們自己每一個人的真實面貌,以及這個城市的「磊落真誠」:
「所以磊落真誠的生活和謊瞞騙隱的生活是交織在一起的。磊落真誠的生活是受壓抑的選擇,目標是達致真誠境界。而謊瞞騙隱的生活,卻是在追求這個目標的過程中,虛與委蛇的回應。」

演出劇目:鐵行里
演出地點:西九文化區Freespace自由空間
主辦:前進進戲劇工作坊
觀看場次:2022年5月18日下午八時正
劇照截圖自宣傳短片:https://fb.watch/d5vgVjUG58/
上次講前進進的演出,原來巳經係2010年的Hamlet b. – 與歷史連結的軌跡。
![]()